過去章節一覽:
第一到第二十一章一覽
第二十二章/大難不死
第二十三章/邪靈科技
第二十四章/金盆洗手
第二十五章/恐怖份子
第二十六章/沒落毒梟
第二十七章/嫉妒之心
第二十八章/大偽善者
第二十九章/大預言家
第三十章/焚城之夜
《永遠的冬天》小說公式站|The Winter Hymn

[HR]
※本章含陰謀論,慎入※
[HR]
房屋與傾危的建築混擠亂堆,頹樑外露,盤根錯節。纏著冒走火電花的電線纏繞私接水管線,猛滲著髒水,看著像某種活物的黑觸角群聚盤纏。
「這該不會是什麼陷阱吧?」克里莫夫循著先知的線索,卻來到貧民窟中。
他躊躇地在莫斯科郊外的破銅爛鐵迷宮中旋繞,對轟動此夜的尤可斯石化工業總部遭縱火事件,一無所聞。
斜風中傳來細細的收音機聲「尤可斯方面沒有發表任何聲明……嘶--嘶--公司的負責人尚未返國,確實的損失數字必須……嘶--聖彼得堡市中心封鎖區,官方呼籲民眾……」
太過使民眾群起瘋魔的事情,他與瓦洛兒都下意識地諱看。各國情治單位探員們熟稔於心的政局暗號,與歷史課本與新聞媒體炖成的一鍋雜燴,版本不同,因此面對國內外事件,他們與人民感到嚴重的點也不大一樣。有時探員們能在鬧哄哄的速食館中,對著牆上電視一則刻意被大事化小的消息猛然肅立,但周圍的人麻痺了似的;反之亦然。
就像陰陽兩界,彼此存在的次元不同,卻空間重疊。人民是人,他們是鬼。鬼能弄人,陽人懼之;日光斗現,魂飛魄散,徒留罵名。
多麼哀傷。
聖彼得堡風中飄著冷淡的雨雪,氣候越往南越趨於大雨,已在莫斯科下成一片老淚縱橫,越晚雨勢越大。
克里莫夫身披暗綠色的雨風衣,決計不能相信貧民窟淨往外堆的回收輪胎、鐵板破推車、垃圾叢林中藏著史可拉托夫參謀長的居處。太大意了,「有人」盜走了他的辭呈,將公文袋抽掉了內容物,剩下的牛皮紙謹慎地入了碎紙機,流入垃圾桶。也許對方認為克里莫夫發現了國防部底下的大黑幕——
克里莫夫暗想,誤會大了。他只想抹去於世上存在的證明,背水一戰,帶走他的情人。他已經知道得夠多、太多了。英國軍情五處頭腦燒壞成為任務機械,功夫卻了得的小探員,光這個人,就意味大量汙黑的貓膩在裡頭。別處再有天大的黑幕,他都沒興趣知道。
他早應該把清潔工捉起來盤問,但假使他和英國MI5傻小子是同一型……他不會形容是什麼,那麼拷問也沒有用。他讀人術下的結論,是這些老鼠人類機械,不是大門深鎖,鑰匙往河裡一扔的牢房,而是本身就莫可奈何的死絕胡同。
「史可拉托夫上校也進了光明會嗎?要是如此,為何願意將被出賣的KGB探員們救出火坑?如果上校非光明會眾,那個清潔工是怎麼回事?難道荷洛維茲老貨,把瓦洛兒與我都騙進去了?不……上校擁有先知的名號並非一天兩天了,他是一位與別的官格格不入的軍官。」
忐忑與疑懼之中,克里莫夫鎮定地從懷中揣出偵查神器:寶石鑑定單眼放大鏡改裝成的微型紅外線偵熱夜視鏡。單眼目鏡掛右眼,綠光映入眼簾——前方沒有可疑的武器或機械運轉。左裸眼目測沒有路燈。每隔三五大步,才一枚好幾戶人家共用的破爛門前燈。
克里莫夫心中疑惑未解,且走且想,一閃神,被一個從巷眼裡竄出,窮極生瘋的乞丐撲上身:「先生!先生!賞我一點東西吧!」老乞丐喘咻咻地喊,劈手摘掉他臉上的紅外線單眼目鏡,也不知搶到什麼,歡喜不迭,手腳並用扒著泥水逃走。這老漢來勢超出常人,簡直不要命,防不勝防。
克里莫夫咒了一聲,如果真死在貧民窟裡,那就十分糟糕,看這窮漢的光景,大概三兩下就被支解了食之。勾索從袖中竄出,他飛簷走壁,順著確定無害的路線,在無限堆積拼湊加蓋的老鼠之屋縫隙中,凌空拐彎抹角地前行。
史可拉托夫的藏身處位於貧民窟核心一座沒落的三級國宅中,外觀骨稜稜的,儼然只賸下水泥的骷髏。公寓建築體四面圍住中空天井,「井」字形空橋連接八方住戶,設計不良,容易走迷,三級國宅淪為四級。從樓高處望下一看,天井直通建築物底部,排水不良的傳統市場一覽無遺。它勉強算露天,但遭圍困,毫無採光,一片陰濕的腸胃。屠戶掛著豬隻還是什麼生物的內臟死體。
多數民眾不願住在這裡。至於底下的市場,因經常有人從高空望下丟包垃圾,不堪其擾,撤攤不少,就剩豬牛販子們據地為王,就地開宰,恐怖異常。
克里莫夫估計著當初貧民窟便是圍繞、仿造著這半墟殘的失敗國宅,緊密地菌集生長起來。可能存在著失敗的地下機關餵養這裏,也未可知。他不願老實的踏著動物血水從一樓往上走,從三樓入侵,勾著空橋往上翻飛,三兩下來到頂樓的八樓。
「這是怎麼回事?」
眼前的景象使克里莫夫大吃一驚。一盞燈炮在暗幽幽的狹道盡頭閃爍,照亮被亂潑油漆,寫滿嘲弄字眼的一扇嚴嚴實實七道鎖鐵門。克里莫夫走近細看——「窮鬼上校快還錢!」、「官做得那麼大,快把羅蔔還我,白癡」、「史可拉托夫,你把錢都花哪去了!」
正要撳鈴,只見門鈴早就被人拔走了,史可拉托夫上校的門牌上,「上校」字樣被塗去改成「窮鬼」,一個紅箭頭,下面用油性筆寫著「再不還錢,下次拔走你的燈泡」。但這些討債字樣中並沒有突出的憤怒與惡意。克里莫夫正覺得十足怪異,猶豫納罕之際,門欻的一下扇開,那七道鎖竟然只是幌子。
比克里莫夫個頭稍矮,姿態微微往前駝傾作沉思狀的史可拉托夫,穿著尋常天藍色襯衫,看也不看地道:「蠢貨,竟然遲到這麼久!你看起來眼神很正常,度數應該在睡鼠以上吧?進來。對了,你叫什麼名字?」克里莫夫才要回答,上校卻接連著道:「差點忘記,我已經知道了,葛雷格利‧克里莫夫‧班茲門諾。」
這麼多年過去了,上校給克里莫夫的第一印象,是在課堂以外的私底下很神經質。
往室內走去,克里莫夫眼前一花。暗地裡,房中構成疊床架屋的雜物,與影子之中奇妙的五顏六色,侵襲來訪者的視覺,還有一種資源回收垃圾特有的成分複雜的花黴味。在這一地亂物中彷彿有一對動物般的年輕女人,貓縮在其中,瑣碎地做著分類。
「你也知道,睡鼠被救出來之後,不管他們之前本領多麼大,要再度適應社會很難,只能做些最底層的工作。要是史瓦利的技術再好一點就好了。」史可拉托夫頭也不回地道,「史瓦利這個從美國來的生活白痴,本身就是位操縱手,你大可不必擔心腦子被他燒掉,但我要看你是不是擁有覺悟。『自由』沒有你想像中的簡單。」
操縱手,睡鼠云云,克里莫夫不了解上校在說什麼,便默不作聲地裝懂。克里莫夫既然都見到了史可拉托夫——經KGB讀人術評估的結果,他確定對方是本人沒錯——他絕對不能放棄這個機會。
僅能稍微容人通過的房間盡頭,唯一充足地沐浴在檯燈光源底下的,只有史可拉托夫的辦公桌。上校似乎將克里莫夫當成不知道自己來這幹什麼的人,不給他發言的餘地,自顧自地滔滔不絕地講起來:「逃出光明會,奔向自由;你追求自由嗎?你配得上?
一般人也許以為打破了所有的界線與標準等同於自由,到了最後,『享樂』成為需求、演變為強制活動。如果有誰不願老實消費社會提供的享樂,或自覺無法如猴子般享樂,相信每年換名車的『社會成功人士』那種價值觀的人將對他報以關切的眼神,要他把原本應該拿去『追逐流行、紓解壓力』的錢,拿去耗在精神治療上,因為你這人無法『自由』,肯定精神有問題。
為了破壞傳統價值而破壞,就像友邦老中國共產黨為了文革而文革——一場空。人類消磨掉本身的價值、精緻文化的骨幹。人類感受不到生命自體價值,以為宗教與道德只有社會學意義,純粹限制表象行為,以免人如動物,無所不為。
出身光明會的學者,除了隱瞞人類科學革命的先導,絕大多數是神祕學術師之外,還甚至隱瞞原始的宗教僅僅試圖用語言『模仿』、『陳述』生命的自體價值這件事。從前的人明白我們被強制遺忘的事:宗教是方法,不是目的;宗教非要憑複雜隱晦,甚至儀式化的『方法』來輔助陳述,因為智慧的產生極端奢侈。只能用個體的靈魂慢慢淬煉,與智慧相比,足以使用文字作為載體的哲學也不過是個次品。
當方法本身變質為目的,光明會扶植的基督教勢力就像病毒一樣到處繁殖。當劣化的宗教再也不能服人了,似是而非替代品『主義』便四處頂著啟蒙的大纛拉人入股。
人類再也沒有『存在即是存在』、『活著即是活著』的自然尊嚴;看到被秘密組織與幾個世紀以來政治利益,反覆翻竄過的基督教結局為何,人們變得沒興趣去尋求這種尊嚴了。偏偏『我活著的目的是什麼』是所有人的問題,彷彿答案該是送的,問不出所以然,不少懦弱者原地乾嚎,像全世界都欠他。但真給了他一個存在目的,又嫌造物待他如零件。偏生有一種專門研究此半死不活現象的主義,叫作『存在主義』。尼采本身是秘密組織土星兄弟會的成員,剩下那批『哲學家』,我能評價什麼?
革命家也好、哲學家也好;如果有誰站出來承認:『對,我們身後有秘密組織的人脈!我們在教科書上留名,的確有順隨秘密組織歷史策畫者的毛摸的嫌疑。』如此,我反而能感受到這些有志之士的思想給他們的生命造就底蘊。
但是沒有。他們沒膽。活著落魄沒關係,人死能留名比較重要。智慧是宇宙,服膺於萬物,萬物服膺之;哲學終歸只是萬物,僅服膺於世界觀自我鞏固。
人類開始覺得有必要歸化某些陣營,否則感覺真理遍地不可尋、活著沒有價值,平白給暴君政府或私德可議的學者們當棋盤棄子。這兩種愚昧者,一方說對方天真、理想主義,另一方說對方頹廢、政權走狗,各自頂著主義去『解放』別人,我對他們的思想本身不予置評,只是他們自由了嗎?
自由沒有那麼廉價。
當人類失去神性,羅素一族那種神職人員應運而生;當人類失去自由,社會精神狀態摩擦生熱產生氾濫的個人英雄主義,娛樂產業滿足大家當英雄的淫猥想像。至於亞斯特一族的媒體王朝,對戰爭的解釋永遠是『天時地利人和一切偶然摻和,反正就打上了』,近代史竟又使用這類廢料充作史料堆疊而成……接下來,某些人開始覺得可以對人類為所欲為,做新世界的神完全可行。
自由即神。只允許一小部份人成為『神』的必要條件,是其餘人類自發性放棄神性,困宥於現實之中,當一隻追在枝微末節幸福屁股後面猛跑的機械老鼠,踏在大企業的齒輪中原地打轉,腦殼空洞,把歷史設的局,當作是自己的選擇;把偉人嘴裡的鬼話,當作自己的思想。
我一開張就說了那麼多廢話,只是希望你不要打著自由無價的口號,指望我和史瓦利無條件救你。我們不會向你討對價關係,只是『自由』極端困難……如果人們以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自由,人類文明就完了。
自從光明會被戈巴契夫引狼入室以來,我發現我認知的人類本質上的自由,與拿民主畫大餅的傢伙口中的自由,相差南轅北轍。我們救出的睡鼠少之又少,許多小鼠承受不住自由的重量,回頭向光明會自首,下場都不好。愛麗絲與桃樂絲,通常只能看他們的造化,以及與史瓦利的緣分如何了。幸虧我們沒被出賣過,大家都是好孩子……」
史可拉托夫一個勁說到後來,戛然而止,有如多年積壓一次洩洪完畢,像洩了氣的皮球,臉色蒼白地默坐在辦公桌後面。克里莫夫像一尊挺直聳立的巨石靈,上半身隱沒在檯燈光暈力有未殆的陰影中,形成更大的陰影。上校知道這位遠古巨物般的男人,藏在層層影子底下,在觀察他。
他也許在看長官方才那一席話,是否只是心理戰術。也許連這間破屋都只是個心理戰術的局子。就像有許多屆才剛踏入軍事學院的孩子,第一天起便被教務處軍方大老葛洛柯夫以各種心理招數哄拐騙嚇,最後他們只相信KGB傳授的讀人術,不相信人類的真誠。史可拉托夫長長地嘆了口氣。他是當真這麼窮,不是陷阱,並非戰術。
「從實招來吧,你究竟是什麼?睡鼠嘛,不可能。胡桃鉗士兵,你的體格很像,但是人太精了。能夠被光明會勢力保送進養工處,你是三月兔吧?知道自己的操縱手是誰嗎?知道的話就最好了,那會省掉史瓦利很多工夫。」
「請問,您不是每位被出賣的探員都願意救嗎?」克里莫夫小心翼翼地繞過他的問題。
「你的確有點像三月兔。」
史可拉托夫用兩隻手指揉了揉眉心,接著拉開抽屜,拿出一疊東西,順手灑在桌面,那些公文隨即整齊有致地攤開,可見當官當得很熟練:「不然你解釋一下這些是怎麼回事好了。」
克里莫夫這才恍然,原來是先知半路截走他的辭呈。史可拉托夫補充道:「你為何硬要離開別人拚死也想擠進來的地方?我看你碰壁不少,現在你應該終於搞清楚國防部底下的所有肥缺,不是誰能進來就進來,更不是可以說走就走的。你算是一個小心的人,KGB畢竟沒有白待,但還是引來了一些不必要的注意,我既然免費幫你擺平這些,你得給一個理由說明這種行為。」
「我要逃,逃得遠遠地,消除了自己一切存在痕跡,從不存在開始,一點一滴重建我倆活著的證據,連全世界的歷史都拋棄,無論要我付出什麼代價。這個看似美好的職位,於我不過是個墳場。」克里莫夫幾乎難掩聲音之中輕微顫抖的柔情,「我要帶著瓦洛加‧亞歷山大維其一起遠走高飛。」
史可拉托夫倏地起立。圍繞辦公木桌的空間區塊,時間靜止住。克里莫夫感覺先知的洞察力,在來回透視他瞳孔深處的靈魂。
史可拉托夫良久才道:「我不能接受。亞歷山大維其是前局長最大的一筆爛帳。安卓波夫人格破產這件事也好,他作為高級將官的選擇也罷,我無力處理這筆業債,此外……」史可拉托夫艱難地頓頓,「這對其他拖著靈魂,靠自我意識求我帶他們尋求自由的底層光明會眾而言,十分不公平。我必須優先肩負他們。」
克里莫夫大步繞過桌子,跪在史可拉托夫面前,拖住他的膝蓋:「上校,求您了!我的願望很卑微,就算能為瓦洛兒做到的有限,我的寶貝必須此後永不見天日,我也願意養著他,直到生命的盡頭。」
見史可拉托夫沒有反應,克里莫夫甚至不顧男性尊嚴掃地,反覆、執拗地哀求他:「上校,瓦洛兒多麼可憐,我想救他,已經走投無路……」說到最後,聲音逐漸微小,男人沉痛地磕頭下去。
史可拉托夫冷笑道:「那麼亞歷山大維其為什麼不親自來求我?你又不是他,你怎麼知道他可憐?更多會眾是利權雙收、度數猛漲、名望上等、人格下賤,享受得要死。」
說畢,便老著一張臉,任憑男人極盡懇求能事的纏著他,逕自拉開椅子坐下,扭開電視。夜已深,國營電視台節目全數播畢,黑白電視中,只剩下深淺不一的無訊號條子掛在螢幕上,發出長長的嗡——的聲音與背景一片白噪音。
史可拉托夫若無其事地看著「電視」,良久,見克里莫夫完全沒有放棄的跡象,不耐煩地道:「你怎麼還不快滾!」
克里莫夫依然糾纏地跪在地下,低聲道:「您也許希望,他們激發出對自由真正的意志,藉此判斷光明會眾是否仍然有靈魂。但即使瓦洛兒的靈魂已經下了地獄,我依舊要將他從地獄的深淵中復活,因為他的靈魂一直活在我的心底。在別人眼中他再怎麼下賤,於我都沒有差別。」
克里莫夫見史可拉托夫態度堅定,對他的哀求與瓦洛加的苦難毫無反應,一咬牙,道:「這附近死角非常多,雖然是很好的藏身處,陷阱也格外好設。一路過來,我在路上扔了不少微型詭雷。」見上校臉部表情動搖了瞬間,他知道威脅奏效,「無論您是否真的窮到住在四級國宅裡,您在這裡應該有不少彼此幫助的好朋友吧。」
在史可拉托夫門上噴漆的顯然不是真正的討債集團,而是先知奇奇怪怪的朋友不少。窮鬼之間朋友相借,誰都熬不起對方久欠。「貧民窟中有與上校彼此依賴的裡社會」克里莫夫迅速做出這樣的評估。
史可拉托夫慢慢地道:「好吧,我明白了。」
克里莫夫以為燃起了一線希望,不料先知冷冷地道:「你根本是個被愛沖昏頭的瘋子,既然這樣……」
高大的男人頓感不妙,正想與上校分辯,只聽見史可拉托夫陡然大喝一聲:「抓住他!戴娜貓們!」
克里莫夫即刻退回雜物中的一小片空地,架起防禦姿勢。周圍只聞飄忽的喵喵之聲,原本還在資源回收的一雙模糊女影立馬閃近克里莫夫背後,雙人左右展開一張大件的精神病院拘束裝。
「我們原本是西德的女武警,喵~」一貓道。
「但是後來被佔領西德的英國皇室共濟會軍方,騙進NATO當慰安婦,喵~」另一貓道。
「我們接受的心智控制,是愛麗斯夢遊仙境系統中的戴娜貓,喵~」
「你的俄語好像有德語口音喵,你們這些東德KGB,不要以為柏林圍牆的另一頭日子很好過啊!喵!吃我們這招白餅皮包大棕熊!」
兩名女子的身法貓形甚重,彷彿真是一雙白貓聯合叼著拘束裝。二人輕盈地捉著厚重的硬麻織帶,將克里莫夫團團圍繞,越轉越緊。克里莫夫知道當她們抓穩時機,一手一搭彼此接住對方的束帶兩端,把帶子收住,就萬事休矣。
「呦,認真防禦呀?沒用的、沒用的喵!」
「乖乖變成餡餅熊吧喵!」
克里莫夫當下先蹲穩馬步,聽她們的位置,憑KGB基礎功夫料貓們的來勢,一手凌空捉住拘束裝垂下的束帶,另一手穩穩拿住上緣的扣環,熊吼一聲,上臂畫出一對半圓,使出蠻力往內一收。紅頭髮的戴娜貓們的包圍攻勢被攔腰截斷。克里莫夫麒麟臂大旋幾圈,要將她們迫得收腳不住。貓們還來不及暗叫不好,便乘著兇猛的離心力雙雙撞在一起,又被繞得頭昏眼花,最後遭男人扔向牆角,被塌下來的紙類回收物砸得滿頭滿臉,堆坐在一塊兒。
「喵嗚,好厲害的男人,跟我做愛吧!」一貓快速爬出紙堆,對克里莫夫報以仰慕的眼光,拱起身要蹭他的腿。克里莫夫提防有詐,靈活地避開。
反應較慢的另一貓這才從雜物中穿出頭來,發出怪聲:「嘶--嘶--臭母貓滾開!他是要跟我上床才對!」
此貓竟活靈活現地哈氣炸毛。克里莫夫從未見過女人可以貓態如此之重,正看得暗自納罕之際,只感覺輕而無痕的微風拂過來,即刻護住頭頸與胸口,史可拉托夫已然欺近身前。
「我都看清楚了。你這不是演技,也不是光明會的替身前來套我的底。你是真正不折不扣的瘋子。三招之內教你倒下。」
手掌在克里莫夫雙臂肌腱脆弱處著力,輕盈地攻擊幾下,克里莫夫登時防禦弛懈,門戶大開。「這是第一招。」上校道。克里莫夫一凜,即刻轉守為攻,朝上校收招之間的破綻出拳。不料史可拉托夫在武術之間轉換自如,柔術的借力使力法,令克里莫夫的重心往前偏斜。
「這是第二招。」
男人原本不至於不濟至此,只是一招熟悉的柔術使他憶念戀人,心神蕩漾。史可拉托夫見機不可失,旋即把他摔出去,壓制在地。
「這是第三招。你以為亞歷山大維其的柔術是誰教的?我當然想救我帶過的所有學生,不是不為,是無奈也。你果然抵不住三招,這才是先知流的心理戰術。」說著,從懷中抽出那支被乞丐扒走的紅外線單眼目鏡,塞回克里莫夫的口袋,「這東西做得真精緻。詭雷你個王八蛋,你的技術水準會只做得出詭雷?下次說謊,請挑個好一點的謊。」
戴娜貓們手忙腳亂地用精神病院拘束裝,把克里莫夫團團綑起來。女武警的逮捕功夫,令克里莫夫拿她們沒轍。史可拉托夫則在一旁對著二貓碎念,明明已經不會再被任何操縱手控制了,每次把她們放回正常社會,她們就順著戴娜貓的本能又跑去做特種行業,這樣下去怎麼得了?還不如來學窮人們做做資源回收,修身養性。貓們顯然聽膩。
「上校大人,現在我們要拿他怎麼辦?」一貓收腳箱坐在克里莫夫的背上,抬頭問道,任憑綑成春捲的男人在她屁股底下掙扎。另外一貓蹲踞在克里莫夫的腿上,用手背洗臉。
「那還用說,瘋子就該送進療養院。」史可拉托夫用手指掐掐眉心,嘆道,「等雨勢小一點,我們就動身。」
不料這雨簾越灑越綿密,直到東方發白才稍歇。兩隻戴娜貓輪流睡覺遊玩,不給克里莫夫任何逃脫的機會。
***
「好吧,經濟學家先生,我得立即控制你的焦慮發作。喂、喂,我說不行!我不能給你那種藥。」
一頭淡金髮色的男人,在病歷表上畫東畫西,槓掉好些東西。他眼前穿著病人服的學者大叔見狀,各種不配合。
「聽好了,我不管你在你的領域得過多少學術肯定,你現在不過是個自制力奇低無比的小鬼!藥呢,會抑制你神經細胞中的物質受體,一旦你開始恍惚,『紅心國王』會藉機變得強大,我們就前功盡棄了……不不,我跟你挑明白了講吧!催眠也不行。解除心智控制本來就辛苦,以後你還得過上沒名沒利的日子,堅強一點行不?」
經濟學家聽見無法用外來的輔助,使體內的怪物安靜,原地躁動。他的心智控制被拆了,大半人格也得重新來過。
史瓦利隨他鬧去,拿出一本厚厚的簿子,推推粗框眼鏡,自顧自地道:「不然我給你念念你先前教我的東西。我照本宣科念什麼,你聽什麼;就像床邊故事,聽到你無聊為止吧!你必須靠訓練意志力,使精神放鬆下來。」
哭鬧的前歐洲國家總統幕僚經濟學家聽了,原本只是躁動,這下子開始胡言亂語兼拍打史瓦利。一頭淡金色長髮的男子和史可拉托夫彼此打鬧慣了,不理他,清清喉嚨,開始唸流水帳:「好喔,銀行的資產負債表--
別人欠銀行的債,就是銀行最主要的資產。只要不斷貸款,資產的部分就會不斷增加。但是後果就跟美聯儲濫印鈔票的一樣,金錢的流動遠大於實質產業的活動,貨幣變得不值錢。當貨幣的價值下降,會導致通貨膨脹,當貨幣價值降到導致實質產業活動出現破綻,人民就變得不願意花錢、產業資金流動(liquidity)驟減,必須通貨緊縮,貨幣量暴跌。
貨幣流通速度降低,用貨幣撐出來的經濟必定陷入不景氣,民眾往往周轉不靈,付不出貸款利息,具有實質價值的物產,比方說抵押的房屋,就會被銀行沒收。這種好康就是國際銀行家所謂的『剪羊毛』;接著,付不出利息的人變多了,大家的債務信用變得不好,銀行提高利率以應對風險,貸款的成本變貴,企業周轉變得更困難。
真實的銀行拿儲蓄人的存款作『部份準備金』,貸數字更大的款項給下至個人,大至國家,卻沒人見過銀行直接與儲蓄人交涉,說服儲蓄人借給別人錢;貸款業務並不辦這種破事兒。所以銀行對市場中究竟存在多少貨幣,影響力非常直接,卻不是像課本上教的一樣,是儲蓄者與週轉者之間的媒介。銀行與貨幣流通的掛勾如此之深,大多數銀行都是『大到不能倒』。
容許私人如此控制貨幣,那是因為以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為首的經濟學家,將資本主義與民主意識型態,這兩個不搭調的東西硬兜在一起,以一種順水推舟的破爛邏輯,把所有無論應該或不該國營的東西國營,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。柴契爾夫人一上任,就是放棄所有的銀行管制……」
該經濟學家一聽到世上其中一位「紅心女王」的名號,像彈簧一樣蹦起來,一邊尖叫一邊從門沒鎖好的精神治療室暴衝出去。
「糗啦!我在幹啥?政府對外的經濟策士,最常見的心智控制『紅心國王』,潛意識的基本設計,就是恐懼總統與跨國銀行總裁!」史瓦利大跳其腳,「大爺我都將這貨解除到了這個地步,居然還犯這種錯誤!我快要跟史可拉笨蛋一樣蠢了!」
史瓦利曾經在CIA作機密情報文官職,是個不輸史考列特的操縱手,運動神經卻很糟,一點美國中情局的款兒都沒有。他長手長腳笨拙地追出去,筆直撞上好幾個早班女護士,順手牽羊地摸了她們的胸部。
「啊呀!色狼四眼田雞醫生!」
「別嚷別嚷,快點喊幫手來,把那傢伙抓住!」
史瓦利故作無辜地道,卻又伸著高挺鼻樑聞了聞鹹豬手,暗道:「還是俄國跟東歐妞正,比一人一對假奶的美國妹好多了。」
騷亂以及東西翻倒的聲音,隨著奔跑中的經濟學家四處擴散,許多還沒醒透的安養院老人都揉著睡眼走出來看。史瓦利急得不得了,這座病院裡,每一瓶生理食鹽水都是要錢的。但隨著蘇共政府慢慢地瓦解,笨上校透過軍方偷撈經費的速度越來越慢了。
鬧了半天,最後是一位男護士,和一名曾經身為CERN科學家的先生,一人一邊架著,把踢騰個沒完的經濟學家抓回史瓦利身邊。
「操縱手……呃不,我知道您不喜歡被這樣稱呼,恩,史瓦利醫生,我覺得我快要沒機油了……隨時會死掉。」科學家忸怩地道。
「你不是沒油,是他們當初在你身上進行鐵皮人心智控制的時候,電擊過頭,你有點腦傷,容易昏倒罷了。誰叫你接光明會偷夾在太空計畫裡的機密研究?大爺我知道你這人愛科學,但人不作死就不會死。好啦,你的學生們快醒來了,去準備你的課,去去。」史瓦利擺出「我的病人都是傻子我頭大」的無奈表情,揉揉額頭。
「可是老人們嫌我講的太難,睡鼠們又沒反應。」鐵皮人科學家委屈地道。但史瓦利沒聽,死活拖著經濟學家,一腳踹開治療室的門,又碰的一聲把門關上、反鎖。科學家望門興嘆。
診療間內,學者沒學者樣、醫生沒醫生樣,兩人零傷害力地彼此扭打,菜雞互啄。醫生叉住經濟學家的鼻孔、學者揪住醫生的領帶。史瓦利胡亂道:「好好好,剛剛說到銀行濫放貸款;得來容易的錢,的確能夠造成短暫的榮景。比方說,被利率極低的貸款沖昏頭的冰島漁夫,跑去買了兩塊地跟一棟豪宅……等到這些地與豪宅被銀行沒收,國家崩壞之後,別國政府大可以在一旁放風涼話……給我冷靜下來!」
經濟學家煩躁蹦跳不已。史瓦利見他壓不住,順手將病歷寫字版朝他頭上揍了一下。經濟學家依然蹦跳不已。
「講完資產,現在講負債。負債恆等於你身上『屬於別人的東西』,所以存款人的錢相當於銀行的負債。奇妙的狀況出現啦!銀行的資產是他人的負債,但別人的財富就是銀行的負債。
資產減去負債的空間就是『權益(equity)』,它們能換算為股東持有的股份。權益歸零,股東的老本敗光,企業歸於破產。因此負債跟權益的比值就是『槓桿』,槓桿就是你能冒多少『風險』。銀行的資產好壞取決於貸款獲利。這時候問題來了--
若借錢者的信用評等很爛,借錢給他的風險高,他付出的利息必然很高,那麼它就是個營收很好的好資產。如果信用評等好,貸款給對方的利率就低了,那麼這是個壞的資產。如果我希望資產好,借錢的人的信用評等必須爛,那麼風險就必定高。但是既然你的資產好,你的槓桿就大,就可以去冒更大的風險。所以風險永遠只有越積越多,絕對不可能控制風險。
風險不外乎賭兩種,賭未來,賭一個東西或一家公司的未來是飛黃騰達還是一壞塗地,這是期貨與股市;賭債信,這沒什麼,就是賭某信用評等極爛的傢伙,還得還不出貸款本金。
『衍伸性金融商品』就是在賭債信。某甲的信用很爛,我這家銀行十分擔心他賴帳,於是我廉價賣掉某甲的一部份債權A,你可以平白無故收取高額利息,條件是,當某甲到期還不出本金時,你要賠償我。就這樣,銀行不管貸款給何種白癡,都沒有無人還錢的風險。
你買了A之後,吃了半年的利息,覺得賺飽了,還可以把A轉賣出去,賣給了老王。老王心想,你當我恐龍嗎?甲的債信這麼爛,又已經被你啃過半年。於是你心生一計,把某乙的債權B整個賣給老王,雖然B風險很低,故沒那麼好賺,至少乙一定會還本金。於是A+B變成了C,老王終於心甘情願買下C。
問題來了,某甲與某乙不見得是人,有可能是某產業的一群企業,整個國家,甚至一大批無能力清償,依舊貸款買房的受騙三級貧戶;你跟老王也不見得是散客,而是投資銀行,國家央行,或金融操盤公司。這些一個一個衍伸性金融商品被東包西包,包到後來,可能成份複雜,龍蛇雜處,亂七八糟,根本不知道誰是誰,每一包看似是划算的投資,每一包都是炸彈,因為它們本質上只是債在丟來丟去而已。
債務包裝,逢戳必爆。差就差在去戳誰,在什麼時間點戳。按照權力者的計畫發動金融風暴並不難。所有一次大爆類型的垮臺風暴,核心精神只有一個——就是某甲某乙,你我以及老王,根本沒人知道『誰能清償債務,誰該清償債務』。不斷加料的巫婆湯的設計宗旨,屬算計風險,以吃利息。既然這樣,那就乾脆爆那個最後被戳的人,大家分屍;看看雷曼兄弟那間百年老店,萬一事情來了,也不能倖免哪;其他銀行家則飽餐一頓之後毫髮無傷。只要涉足與金融沾上邊的光明會家族,財富永遠源源不絕。
至於被分屍的那位又如何?根本不知道誰還得出債有兩個結果,片面減輕這家金融機構的負債,那麼存款人或投資人的錢就人間蒸發。要不然就重整它們的資產負債表,那麼它們的資金就會凍結。偏偏它們全都『大到不能倒』,一定要保持運作;那麼惟有用納稅人的錢填補虧空一途。所以就算被分屍,還是有紅可以吃。」
史瓦利憋著一口氣一路唸完,經濟學家已經聽到睡著了。
史瓦利撥了撥落在額前的淡金色長髮,吁了一口氣,道:「真是,你的進步一小步,就是大爺我跨得要死的一大步。拆解完全心智控制者的指令都沒那麼囉唆,偏偏越接近心靈的自由,對意志力的考驗越重哪。」
男護士正雙手端著早餐盤,可能在治療室外頭等候已久,不耐煩地踢了踢門。史瓦利連忙開門,一看,大失所望道:「為什麼不是大波護士妹子?」
「女護士們都不敢接近醫生你。」
男護士無視史瓦利生氣嘟嘴,將麵包與牛奶在一疊疊病例中騰了位子放下,又看了看在治療躺椅上睡著的經濟學家,道:「醫生你只是想讓他別鬧,為什麼不用操縱手指令就好了?」
史瓦利翻看下一個接受解除心智控制者的病例,一邊道:「濫用那種禁錮人心的東西,怎麼可能使人自由呢?史可拉笨蛋常說,操縱手指令的確可以安頓他們,那樣就失去我們努力的意義了。」
男護士正想說他不是那個意思,只是如果史瓦利的病人又亂摔東西,療養院就真的沒經費了。大夥兒最大的金主史可拉托夫,近來談到錢,就索性左手指、右手指把耳朵堵起來,開始啦啦啦。
晨光從輕輕抖動的百葉窗簾縫裡流入,史瓦利穿著雪白的醫師袍沐浴其中,悠哉地圈圈轉他的旋轉辦公椅,一邊用彩虹小馬領帶擦眼鏡。天大的麻煩,史可拉托夫都能化險為夷,總歸沒他的事。
男護士知道上校把他慣得毫無危機意識,講不通,聳聳肩便離去了。
這座僻靜的療養院位於莫斯科西南方,近烏克蘭的清幽隱密處,設備極為先進,用物昂貴。正當的經費來源,只有接受優渥退休俸住進這間療養院的退職文官老人。餘下費用,包括精神科醫護人員,僅剩史可拉托夫獨立支撐。上校總是有辦法在最後一刻生出錢來,維護得相當良好。
「我們治療他們,但不能收前光明會眾們的錢。這些傢伙的帳戶一動,國際銀行家們通通都知道了。我們是盡己之力,解放這個世界。」先知總是這樣告誡史瓦利。
這塊被參謀長劃定的醫療建設用地,受溫柔的松林環抱,差一點被別的大官擄走蓋私人渡假村。一夜暴雨將針葉林洗得蔥鬱。挺拔樹木之間散落細細的白光,將塵霧照成新娘的薄紗,一切靜得像天籟無形,流淌於天地。
史瓦利拉開窗簾,讓層層丘陵低調的綠意透進來。他用這幅景致配早餐,啵兒爽的,樂不思美國。不遠處,一對前凸後翹的儷影現身森林石板小道。門房警衛對史瓦利發出警戒通知。
「不要緊,我已經看見她們了,是笨蛋上校的戴娜貓們。」史瓦利朝著對講機道。
「那我看是她們要警戒你。」警衛道。史瓦利嘻皮笑臉地摩拳擦掌,色狼之右手準備吃豆腐,厚臉皮之左手準備跟笨蛋上校伸手要錢。
[HR]
【參考資料】
John Lanchester 約翰‧蘭徹斯特,大債時代,國內出版社:早安財經
【本章後話】
本圖取自Duncan氏的「共濟會的儀式與管理,第三版(Masonic Ritual and Monitor)」,這是皇室拱門共濟會的「第二階秘法掌管者(Master of the Second Veil)」的儀式手勢,叫作耶布侖使者的隱藏之手(Hidden Hand of the Man of Jabuhlun)。根據C.C. Zain在《共濟會儀式的古文明考(Ancient Masonry)》一書中的說法,此手勢的由來如下--為了使人類也能達成最高等的三位一體,擁有神一般的智能,必須知道「神」除了神G.O.D這個字以及耶和華YHWH以外,第三個失落的名字。這個名字雖然被視為亡佚,但可以用耶布侖Jabuhlun或 Mahabone(希伯來文的意思是「蓋神殿的石匠」)來替代。
耶布侖因此是耶和華賜給新世界的神/超人,他更勝於耶穌,也就是耶和華賜給普通老百姓/羊群的牧者,因為耶布侖這個名字至善,同時也至為邪惡,因此是超越善惡,惡因此等於善的一種表現。耶布侖的使者在世上的任務,就是替「所羅門王」建立新的耶路撒冷。
--Texe Marrs, Codex Magica: Hidden Codes of the Illuminati
雨果 Victor Hugo/玫瑰十字會、錫安長老修士會會眾

法國大革命後的激進份子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(中間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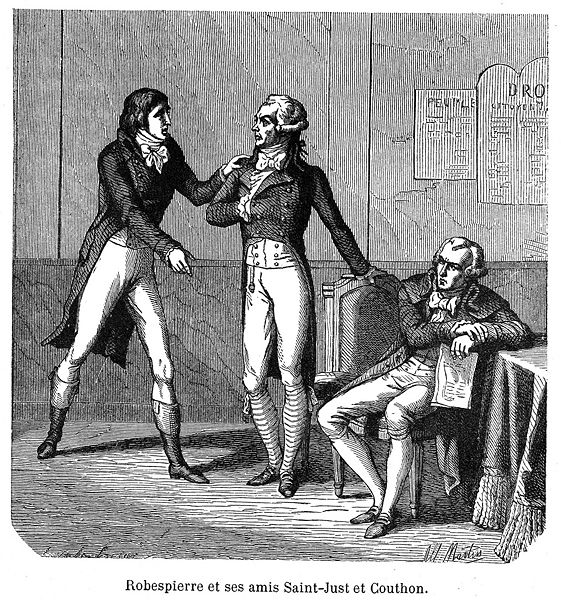
土耳其國父凱末爾

薩羅門‧羅斯柴爾德 /Salomon Rothschild

莫札特(奧地利共濟會支會會眾,據說是貴族會眾Franz von Walsegg 為了警告其背叛,匿名要求他創作安魂曲。安魂曲的創作停在「審判日,悲愴日/Lacrymosa Dies Illa」莫札特即告死亡。)

歌德/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

馬克思/Carl Marx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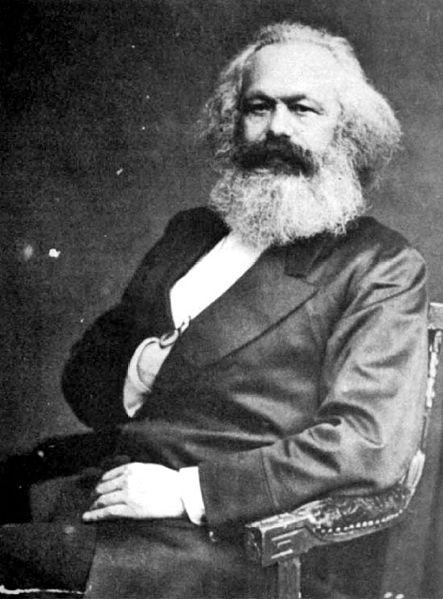
尼采/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(自幼即是會眾)

其餘族繁不及備載。
[HR]
※待續/隔週末更新※
前往下一章節
第一到第二十一章一覽
第二十二章/大難不死
第二十三章/邪靈科技
第二十四章/金盆洗手
第二十五章/恐怖份子
第二十六章/沒落毒梟
第二十七章/嫉妒之心
第二十八章/大偽善者
第二十九章/大預言家
第三十章/焚城之夜
《永遠的冬天》小說公式站|The Winter Hymn

[HR]
※本章含陰謀論,慎入※
[HR]
房屋與傾危的建築混擠亂堆,頹樑外露,盤根錯節。纏著冒走火電花的電線纏繞私接水管線,猛滲著髒水,看著像某種活物的黑觸角群聚盤纏。
「這該不會是什麼陷阱吧?」克里莫夫循著先知的線索,卻來到貧民窟中。
他躊躇地在莫斯科郊外的破銅爛鐵迷宮中旋繞,對轟動此夜的尤可斯石化工業總部遭縱火事件,一無所聞。
斜風中傳來細細的收音機聲「尤可斯方面沒有發表任何聲明……嘶--嘶--公司的負責人尚未返國,確實的損失數字必須……嘶--聖彼得堡市中心封鎖區,官方呼籲民眾……」
太過使民眾群起瘋魔的事情,他與瓦洛兒都下意識地諱看。各國情治單位探員們熟稔於心的政局暗號,與歷史課本與新聞媒體炖成的一鍋雜燴,版本不同,因此面對國內外事件,他們與人民感到嚴重的點也不大一樣。有時探員們能在鬧哄哄的速食館中,對著牆上電視一則刻意被大事化小的消息猛然肅立,但周圍的人麻痺了似的;反之亦然。
就像陰陽兩界,彼此存在的次元不同,卻空間重疊。人民是人,他們是鬼。鬼能弄人,陽人懼之;日光斗現,魂飛魄散,徒留罵名。
多麼哀傷。
聖彼得堡風中飄著冷淡的雨雪,氣候越往南越趨於大雨,已在莫斯科下成一片老淚縱橫,越晚雨勢越大。
克里莫夫身披暗綠色的雨風衣,決計不能相信貧民窟淨往外堆的回收輪胎、鐵板破推車、垃圾叢林中藏著史可拉托夫參謀長的居處。太大意了,「有人」盜走了他的辭呈,將公文袋抽掉了內容物,剩下的牛皮紙謹慎地入了碎紙機,流入垃圾桶。也許對方認為克里莫夫發現了國防部底下的大黑幕——
克里莫夫暗想,誤會大了。他只想抹去於世上存在的證明,背水一戰,帶走他的情人。他已經知道得夠多、太多了。英國軍情五處頭腦燒壞成為任務機械,功夫卻了得的小探員,光這個人,就意味大量汙黑的貓膩在裡頭。別處再有天大的黑幕,他都沒興趣知道。
他早應該把清潔工捉起來盤問,但假使他和英國MI5傻小子是同一型……他不會形容是什麼,那麼拷問也沒有用。他讀人術下的結論,是這些老鼠人類機械,不是大門深鎖,鑰匙往河裡一扔的牢房,而是本身就莫可奈何的死絕胡同。
「史可拉托夫上校也進了光明會嗎?要是如此,為何願意將被出賣的KGB探員們救出火坑?如果上校非光明會眾,那個清潔工是怎麼回事?難道荷洛維茲老貨,把瓦洛兒與我都騙進去了?不……上校擁有先知的名號並非一天兩天了,他是一位與別的官格格不入的軍官。」
忐忑與疑懼之中,克里莫夫鎮定地從懷中揣出偵查神器:寶石鑑定單眼放大鏡改裝成的微型紅外線偵熱夜視鏡。單眼目鏡掛右眼,綠光映入眼簾——前方沒有可疑的武器或機械運轉。左裸眼目測沒有路燈。每隔三五大步,才一枚好幾戶人家共用的破爛門前燈。
克里莫夫心中疑惑未解,且走且想,一閃神,被一個從巷眼裡竄出,窮極生瘋的乞丐撲上身:「先生!先生!賞我一點東西吧!」老乞丐喘咻咻地喊,劈手摘掉他臉上的紅外線單眼目鏡,也不知搶到什麼,歡喜不迭,手腳並用扒著泥水逃走。這老漢來勢超出常人,簡直不要命,防不勝防。
克里莫夫咒了一聲,如果真死在貧民窟裡,那就十分糟糕,看這窮漢的光景,大概三兩下就被支解了食之。勾索從袖中竄出,他飛簷走壁,順著確定無害的路線,在無限堆積拼湊加蓋的老鼠之屋縫隙中,凌空拐彎抹角地前行。
史可拉托夫的藏身處位於貧民窟核心一座沒落的三級國宅中,外觀骨稜稜的,儼然只賸下水泥的骷髏。公寓建築體四面圍住中空天井,「井」字形空橋連接八方住戶,設計不良,容易走迷,三級國宅淪為四級。從樓高處望下一看,天井直通建築物底部,排水不良的傳統市場一覽無遺。它勉強算露天,但遭圍困,毫無採光,一片陰濕的腸胃。屠戶掛著豬隻還是什麼生物的內臟死體。
多數民眾不願住在這裡。至於底下的市場,因經常有人從高空望下丟包垃圾,不堪其擾,撤攤不少,就剩豬牛販子們據地為王,就地開宰,恐怖異常。
克里莫夫估計著當初貧民窟便是圍繞、仿造著這半墟殘的失敗國宅,緊密地菌集生長起來。可能存在著失敗的地下機關餵養這裏,也未可知。他不願老實的踏著動物血水從一樓往上走,從三樓入侵,勾著空橋往上翻飛,三兩下來到頂樓的八樓。
「這是怎麼回事?」
眼前的景象使克里莫夫大吃一驚。一盞燈炮在暗幽幽的狹道盡頭閃爍,照亮被亂潑油漆,寫滿嘲弄字眼的一扇嚴嚴實實七道鎖鐵門。克里莫夫走近細看——「窮鬼上校快還錢!」、「官做得那麼大,快把羅蔔還我,白癡」、「史可拉托夫,你把錢都花哪去了!」
正要撳鈴,只見門鈴早就被人拔走了,史可拉托夫上校的門牌上,「上校」字樣被塗去改成「窮鬼」,一個紅箭頭,下面用油性筆寫著「再不還錢,下次拔走你的燈泡」。但這些討債字樣中並沒有突出的憤怒與惡意。克里莫夫正覺得十足怪異,猶豫納罕之際,門欻的一下扇開,那七道鎖竟然只是幌子。
比克里莫夫個頭稍矮,姿態微微往前駝傾作沉思狀的史可拉托夫,穿著尋常天藍色襯衫,看也不看地道:「蠢貨,竟然遲到這麼久!你看起來眼神很正常,度數應該在睡鼠以上吧?進來。對了,你叫什麼名字?」克里莫夫才要回答,上校卻接連著道:「差點忘記,我已經知道了,葛雷格利‧克里莫夫‧班茲門諾。」
這麼多年過去了,上校給克里莫夫的第一印象,是在課堂以外的私底下很神經質。
往室內走去,克里莫夫眼前一花。暗地裡,房中構成疊床架屋的雜物,與影子之中奇妙的五顏六色,侵襲來訪者的視覺,還有一種資源回收垃圾特有的成分複雜的花黴味。在這一地亂物中彷彿有一對動物般的年輕女人,貓縮在其中,瑣碎地做著分類。
「你也知道,睡鼠被救出來之後,不管他們之前本領多麼大,要再度適應社會很難,只能做些最底層的工作。要是史瓦利的技術再好一點就好了。」史可拉托夫頭也不回地道,「史瓦利這個從美國來的生活白痴,本身就是位操縱手,你大可不必擔心腦子被他燒掉,但我要看你是不是擁有覺悟。『自由』沒有你想像中的簡單。」
操縱手,睡鼠云云,克里莫夫不了解上校在說什麼,便默不作聲地裝懂。克里莫夫既然都見到了史可拉托夫——經KGB讀人術評估的結果,他確定對方是本人沒錯——他絕對不能放棄這個機會。
僅能稍微容人通過的房間盡頭,唯一充足地沐浴在檯燈光源底下的,只有史可拉托夫的辦公桌。上校似乎將克里莫夫當成不知道自己來這幹什麼的人,不給他發言的餘地,自顧自地滔滔不絕地講起來:「逃出光明會,奔向自由;你追求自由嗎?你配得上?
一般人也許以為打破了所有的界線與標準等同於自由,到了最後,『享樂』成為需求、演變為強制活動。如果有誰不願老實消費社會提供的享樂,或自覺無法如猴子般享樂,相信每年換名車的『社會成功人士』那種價值觀的人將對他報以關切的眼神,要他把原本應該拿去『追逐流行、紓解壓力』的錢,拿去耗在精神治療上,因為你這人無法『自由』,肯定精神有問題。
為了破壞傳統價值而破壞,就像友邦老中國共產黨為了文革而文革——一場空。人類消磨掉本身的價值、精緻文化的骨幹。人類感受不到生命自體價值,以為宗教與道德只有社會學意義,純粹限制表象行為,以免人如動物,無所不為。
出身光明會的學者,除了隱瞞人類科學革命的先導,絕大多數是神祕學術師之外,還甚至隱瞞原始的宗教僅僅試圖用語言『模仿』、『陳述』生命的自體價值這件事。從前的人明白我們被強制遺忘的事:宗教是方法,不是目的;宗教非要憑複雜隱晦,甚至儀式化的『方法』來輔助陳述,因為智慧的產生極端奢侈。只能用個體的靈魂慢慢淬煉,與智慧相比,足以使用文字作為載體的哲學也不過是個次品。
當方法本身變質為目的,光明會扶植的基督教勢力就像病毒一樣到處繁殖。當劣化的宗教再也不能服人了,似是而非替代品『主義』便四處頂著啟蒙的大纛拉人入股。
人類再也沒有『存在即是存在』、『活著即是活著』的自然尊嚴;看到被秘密組織與幾個世紀以來政治利益,反覆翻竄過的基督教結局為何,人們變得沒興趣去尋求這種尊嚴了。偏偏『我活著的目的是什麼』是所有人的問題,彷彿答案該是送的,問不出所以然,不少懦弱者原地乾嚎,像全世界都欠他。但真給了他一個存在目的,又嫌造物待他如零件。偏生有一種專門研究此半死不活現象的主義,叫作『存在主義』。尼采本身是秘密組織土星兄弟會的成員,剩下那批『哲學家』,我能評價什麼?
革命家也好、哲學家也好;如果有誰站出來承認:『對,我們身後有秘密組織的人脈!我們在教科書上留名,的確有順隨秘密組織歷史策畫者的毛摸的嫌疑。』如此,我反而能感受到這些有志之士的思想給他們的生命造就底蘊。
但是沒有。他們沒膽。活著落魄沒關係,人死能留名比較重要。智慧是宇宙,服膺於萬物,萬物服膺之;哲學終歸只是萬物,僅服膺於世界觀自我鞏固。
人類開始覺得有必要歸化某些陣營,否則感覺真理遍地不可尋、活著沒有價值,平白給暴君政府或私德可議的學者們當棋盤棄子。這兩種愚昧者,一方說對方天真、理想主義,另一方說對方頹廢、政權走狗,各自頂著主義去『解放』別人,我對他們的思想本身不予置評,只是他們自由了嗎?
自由沒有那麼廉價。
當人類失去神性,羅素一族那種神職人員應運而生;當人類失去自由,社會精神狀態摩擦生熱產生氾濫的個人英雄主義,娛樂產業滿足大家當英雄的淫猥想像。至於亞斯特一族的媒體王朝,對戰爭的解釋永遠是『天時地利人和一切偶然摻和,反正就打上了』,近代史竟又使用這類廢料充作史料堆疊而成……接下來,某些人開始覺得可以對人類為所欲為,做新世界的神完全可行。
自由即神。只允許一小部份人成為『神』的必要條件,是其餘人類自發性放棄神性,困宥於現實之中,當一隻追在枝微末節幸福屁股後面猛跑的機械老鼠,踏在大企業的齒輪中原地打轉,腦殼空洞,把歷史設的局,當作是自己的選擇;把偉人嘴裡的鬼話,當作自己的思想。
我一開張就說了那麼多廢話,只是希望你不要打著自由無價的口號,指望我和史瓦利無條件救你。我們不會向你討對價關係,只是『自由』極端困難……如果人們以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自由,人類文明就完了。
自從光明會被戈巴契夫引狼入室以來,我發現我認知的人類本質上的自由,與拿民主畫大餅的傢伙口中的自由,相差南轅北轍。我們救出的睡鼠少之又少,許多小鼠承受不住自由的重量,回頭向光明會自首,下場都不好。愛麗絲與桃樂絲,通常只能看他們的造化,以及與史瓦利的緣分如何了。幸虧我們沒被出賣過,大家都是好孩子……」
史可拉托夫一個勁說到後來,戛然而止,有如多年積壓一次洩洪完畢,像洩了氣的皮球,臉色蒼白地默坐在辦公桌後面。克里莫夫像一尊挺直聳立的巨石靈,上半身隱沒在檯燈光暈力有未殆的陰影中,形成更大的陰影。上校知道這位遠古巨物般的男人,藏在層層影子底下,在觀察他。
他也許在看長官方才那一席話,是否只是心理戰術。也許連這間破屋都只是個心理戰術的局子。就像有許多屆才剛踏入軍事學院的孩子,第一天起便被教務處軍方大老葛洛柯夫以各種心理招數哄拐騙嚇,最後他們只相信KGB傳授的讀人術,不相信人類的真誠。史可拉托夫長長地嘆了口氣。他是當真這麼窮,不是陷阱,並非戰術。
「從實招來吧,你究竟是什麼?睡鼠嘛,不可能。胡桃鉗士兵,你的體格很像,但是人太精了。能夠被光明會勢力保送進養工處,你是三月兔吧?知道自己的操縱手是誰嗎?知道的話就最好了,那會省掉史瓦利很多工夫。」
「請問,您不是每位被出賣的探員都願意救嗎?」克里莫夫小心翼翼地繞過他的問題。
「你的確有點像三月兔。」
史可拉托夫用兩隻手指揉了揉眉心,接著拉開抽屜,拿出一疊東西,順手灑在桌面,那些公文隨即整齊有致地攤開,可見當官當得很熟練:「不然你解釋一下這些是怎麼回事好了。」
克里莫夫這才恍然,原來是先知半路截走他的辭呈。史可拉托夫補充道:「你為何硬要離開別人拚死也想擠進來的地方?我看你碰壁不少,現在你應該終於搞清楚國防部底下的所有肥缺,不是誰能進來就進來,更不是可以說走就走的。你算是一個小心的人,KGB畢竟沒有白待,但還是引來了一些不必要的注意,我既然免費幫你擺平這些,你得給一個理由說明這種行為。」
「我要逃,逃得遠遠地,消除了自己一切存在痕跡,從不存在開始,一點一滴重建我倆活著的證據,連全世界的歷史都拋棄,無論要我付出什麼代價。這個看似美好的職位,於我不過是個墳場。」克里莫夫幾乎難掩聲音之中輕微顫抖的柔情,「我要帶著瓦洛加‧亞歷山大維其一起遠走高飛。」
史可拉托夫倏地起立。圍繞辦公木桌的空間區塊,時間靜止住。克里莫夫感覺先知的洞察力,在來回透視他瞳孔深處的靈魂。
史可拉托夫良久才道:「我不能接受。亞歷山大維其是前局長最大的一筆爛帳。安卓波夫人格破產這件事也好,他作為高級將官的選擇也罷,我無力處理這筆業債,此外……」史可拉托夫艱難地頓頓,「這對其他拖著靈魂,靠自我意識求我帶他們尋求自由的底層光明會眾而言,十分不公平。我必須優先肩負他們。」
克里莫夫大步繞過桌子,跪在史可拉托夫面前,拖住他的膝蓋:「上校,求您了!我的願望很卑微,就算能為瓦洛兒做到的有限,我的寶貝必須此後永不見天日,我也願意養著他,直到生命的盡頭。」
見史可拉托夫沒有反應,克里莫夫甚至不顧男性尊嚴掃地,反覆、執拗地哀求他:「上校,瓦洛兒多麼可憐,我想救他,已經走投無路……」說到最後,聲音逐漸微小,男人沉痛地磕頭下去。
史可拉托夫冷笑道:「那麼亞歷山大維其為什麼不親自來求我?你又不是他,你怎麼知道他可憐?更多會眾是利權雙收、度數猛漲、名望上等、人格下賤,享受得要死。」
說畢,便老著一張臉,任憑男人極盡懇求能事的纏著他,逕自拉開椅子坐下,扭開電視。夜已深,國營電視台節目全數播畢,黑白電視中,只剩下深淺不一的無訊號條子掛在螢幕上,發出長長的嗡——的聲音與背景一片白噪音。
史可拉托夫若無其事地看著「電視」,良久,見克里莫夫完全沒有放棄的跡象,不耐煩地道:「你怎麼還不快滾!」
克里莫夫依然糾纏地跪在地下,低聲道:「您也許希望,他們激發出對自由真正的意志,藉此判斷光明會眾是否仍然有靈魂。但即使瓦洛兒的靈魂已經下了地獄,我依舊要將他從地獄的深淵中復活,因為他的靈魂一直活在我的心底。在別人眼中他再怎麼下賤,於我都沒有差別。」
克里莫夫見史可拉托夫態度堅定,對他的哀求與瓦洛加的苦難毫無反應,一咬牙,道:「這附近死角非常多,雖然是很好的藏身處,陷阱也格外好設。一路過來,我在路上扔了不少微型詭雷。」見上校臉部表情動搖了瞬間,他知道威脅奏效,「無論您是否真的窮到住在四級國宅裡,您在這裡應該有不少彼此幫助的好朋友吧。」
在史可拉托夫門上噴漆的顯然不是真正的討債集團,而是先知奇奇怪怪的朋友不少。窮鬼之間朋友相借,誰都熬不起對方久欠。「貧民窟中有與上校彼此依賴的裡社會」克里莫夫迅速做出這樣的評估。
史可拉托夫慢慢地道:「好吧,我明白了。」
克里莫夫以為燃起了一線希望,不料先知冷冷地道:「你根本是個被愛沖昏頭的瘋子,既然這樣……」
高大的男人頓感不妙,正想與上校分辯,只聽見史可拉托夫陡然大喝一聲:「抓住他!戴娜貓們!」
克里莫夫即刻退回雜物中的一小片空地,架起防禦姿勢。周圍只聞飄忽的喵喵之聲,原本還在資源回收的一雙模糊女影立馬閃近克里莫夫背後,雙人左右展開一張大件的精神病院拘束裝。
「我們原本是西德的女武警,喵~」一貓道。
「但是後來被佔領西德的英國皇室共濟會軍方,騙進NATO當慰安婦,喵~」另一貓道。
「我們接受的心智控制,是愛麗斯夢遊仙境系統中的戴娜貓,喵~」
「你的俄語好像有德語口音喵,你們這些東德KGB,不要以為柏林圍牆的另一頭日子很好過啊!喵!吃我們這招白餅皮包大棕熊!」
兩名女子的身法貓形甚重,彷彿真是一雙白貓聯合叼著拘束裝。二人輕盈地捉著厚重的硬麻織帶,將克里莫夫團團圍繞,越轉越緊。克里莫夫知道當她們抓穩時機,一手一搭彼此接住對方的束帶兩端,把帶子收住,就萬事休矣。
「呦,認真防禦呀?沒用的、沒用的喵!」
「乖乖變成餡餅熊吧喵!」
克里莫夫當下先蹲穩馬步,聽她們的位置,憑KGB基礎功夫料貓們的來勢,一手凌空捉住拘束裝垂下的束帶,另一手穩穩拿住上緣的扣環,熊吼一聲,上臂畫出一對半圓,使出蠻力往內一收。紅頭髮的戴娜貓們的包圍攻勢被攔腰截斷。克里莫夫麒麟臂大旋幾圈,要將她們迫得收腳不住。貓們還來不及暗叫不好,便乘著兇猛的離心力雙雙撞在一起,又被繞得頭昏眼花,最後遭男人扔向牆角,被塌下來的紙類回收物砸得滿頭滿臉,堆坐在一塊兒。
「喵嗚,好厲害的男人,跟我做愛吧!」一貓快速爬出紙堆,對克里莫夫報以仰慕的眼光,拱起身要蹭他的腿。克里莫夫提防有詐,靈活地避開。
反應較慢的另一貓這才從雜物中穿出頭來,發出怪聲:「嘶--嘶--臭母貓滾開!他是要跟我上床才對!」
此貓竟活靈活現地哈氣炸毛。克里莫夫從未見過女人可以貓態如此之重,正看得暗自納罕之際,只感覺輕而無痕的微風拂過來,即刻護住頭頸與胸口,史可拉托夫已然欺近身前。
「我都看清楚了。你這不是演技,也不是光明會的替身前來套我的底。你是真正不折不扣的瘋子。三招之內教你倒下。」
手掌在克里莫夫雙臂肌腱脆弱處著力,輕盈地攻擊幾下,克里莫夫登時防禦弛懈,門戶大開。「這是第一招。」上校道。克里莫夫一凜,即刻轉守為攻,朝上校收招之間的破綻出拳。不料史可拉托夫在武術之間轉換自如,柔術的借力使力法,令克里莫夫的重心往前偏斜。
「這是第二招。」
男人原本不至於不濟至此,只是一招熟悉的柔術使他憶念戀人,心神蕩漾。史可拉托夫見機不可失,旋即把他摔出去,壓制在地。
「這是第三招。你以為亞歷山大維其的柔術是誰教的?我當然想救我帶過的所有學生,不是不為,是無奈也。你果然抵不住三招,這才是先知流的心理戰術。」說著,從懷中抽出那支被乞丐扒走的紅外線單眼目鏡,塞回克里莫夫的口袋,「這東西做得真精緻。詭雷你個王八蛋,你的技術水準會只做得出詭雷?下次說謊,請挑個好一點的謊。」
戴娜貓們手忙腳亂地用精神病院拘束裝,把克里莫夫團團綑起來。女武警的逮捕功夫,令克里莫夫拿她們沒轍。史可拉托夫則在一旁對著二貓碎念,明明已經不會再被任何操縱手控制了,每次把她們放回正常社會,她們就順著戴娜貓的本能又跑去做特種行業,這樣下去怎麼得了?還不如來學窮人們做做資源回收,修身養性。貓們顯然聽膩。
「上校大人,現在我們要拿他怎麼辦?」一貓收腳箱坐在克里莫夫的背上,抬頭問道,任憑綑成春捲的男人在她屁股底下掙扎。另外一貓蹲踞在克里莫夫的腿上,用手背洗臉。
「那還用說,瘋子就該送進療養院。」史可拉托夫用手指掐掐眉心,嘆道,「等雨勢小一點,我們就動身。」
不料這雨簾越灑越綿密,直到東方發白才稍歇。兩隻戴娜貓輪流睡覺遊玩,不給克里莫夫任何逃脫的機會。
***
「好吧,經濟學家先生,我得立即控制你的焦慮發作。喂、喂,我說不行!我不能給你那種藥。」
一頭淡金髮色的男人,在病歷表上畫東畫西,槓掉好些東西。他眼前穿著病人服的學者大叔見狀,各種不配合。
「聽好了,我不管你在你的領域得過多少學術肯定,你現在不過是個自制力奇低無比的小鬼!藥呢,會抑制你神經細胞中的物質受體,一旦你開始恍惚,『紅心國王』會藉機變得強大,我們就前功盡棄了……不不,我跟你挑明白了講吧!催眠也不行。解除心智控制本來就辛苦,以後你還得過上沒名沒利的日子,堅強一點行不?」
經濟學家聽見無法用外來的輔助,使體內的怪物安靜,原地躁動。他的心智控制被拆了,大半人格也得重新來過。
史瓦利隨他鬧去,拿出一本厚厚的簿子,推推粗框眼鏡,自顧自地道:「不然我給你念念你先前教我的東西。我照本宣科念什麼,你聽什麼;就像床邊故事,聽到你無聊為止吧!你必須靠訓練意志力,使精神放鬆下來。」
哭鬧的前歐洲國家總統幕僚經濟學家聽了,原本只是躁動,這下子開始胡言亂語兼拍打史瓦利。一頭淡金色長髮的男子和史可拉托夫彼此打鬧慣了,不理他,清清喉嚨,開始唸流水帳:「好喔,銀行的資產負債表--
別人欠銀行的債,就是銀行最主要的資產。只要不斷貸款,資產的部分就會不斷增加。但是後果就跟美聯儲濫印鈔票的一樣,金錢的流動遠大於實質產業的活動,貨幣變得不值錢。當貨幣的價值下降,會導致通貨膨脹,當貨幣價值降到導致實質產業活動出現破綻,人民就變得不願意花錢、產業資金流動(liquidity)驟減,必須通貨緊縮,貨幣量暴跌。
貨幣流通速度降低,用貨幣撐出來的經濟必定陷入不景氣,民眾往往周轉不靈,付不出貸款利息,具有實質價值的物產,比方說抵押的房屋,就會被銀行沒收。這種好康就是國際銀行家所謂的『剪羊毛』;接著,付不出利息的人變多了,大家的債務信用變得不好,銀行提高利率以應對風險,貸款的成本變貴,企業周轉變得更困難。
真實的銀行拿儲蓄人的存款作『部份準備金』,貸數字更大的款項給下至個人,大至國家,卻沒人見過銀行直接與儲蓄人交涉,說服儲蓄人借給別人錢;貸款業務並不辦這種破事兒。所以銀行對市場中究竟存在多少貨幣,影響力非常直接,卻不是像課本上教的一樣,是儲蓄者與週轉者之間的媒介。銀行與貨幣流通的掛勾如此之深,大多數銀行都是『大到不能倒』。
容許私人如此控制貨幣,那是因為以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為首的經濟學家,將資本主義與民主意識型態,這兩個不搭調的東西硬兜在一起,以一種順水推舟的破爛邏輯,把所有無論應該或不該國營的東西國營,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。柴契爾夫人一上任,就是放棄所有的銀行管制……」
該經濟學家一聽到世上其中一位「紅心女王」的名號,像彈簧一樣蹦起來,一邊尖叫一邊從門沒鎖好的精神治療室暴衝出去。
「糗啦!我在幹啥?政府對外的經濟策士,最常見的心智控制『紅心國王』,潛意識的基本設計,就是恐懼總統與跨國銀行總裁!」史瓦利大跳其腳,「大爺我都將這貨解除到了這個地步,居然還犯這種錯誤!我快要跟史可拉笨蛋一樣蠢了!」
史瓦利曾經在CIA作機密情報文官職,是個不輸史考列特的操縱手,運動神經卻很糟,一點美國中情局的款兒都沒有。他長手長腳笨拙地追出去,筆直撞上好幾個早班女護士,順手牽羊地摸了她們的胸部。
「啊呀!色狼四眼田雞醫生!」
「別嚷別嚷,快點喊幫手來,把那傢伙抓住!」
史瓦利故作無辜地道,卻又伸著高挺鼻樑聞了聞鹹豬手,暗道:「還是俄國跟東歐妞正,比一人一對假奶的美國妹好多了。」
騷亂以及東西翻倒的聲音,隨著奔跑中的經濟學家四處擴散,許多還沒醒透的安養院老人都揉著睡眼走出來看。史瓦利急得不得了,這座病院裡,每一瓶生理食鹽水都是要錢的。但隨著蘇共政府慢慢地瓦解,笨上校透過軍方偷撈經費的速度越來越慢了。
鬧了半天,最後是一位男護士,和一名曾經身為CERN科學家的先生,一人一邊架著,把踢騰個沒完的經濟學家抓回史瓦利身邊。
「操縱手……呃不,我知道您不喜歡被這樣稱呼,恩,史瓦利醫生,我覺得我快要沒機油了……隨時會死掉。」科學家忸怩地道。
「你不是沒油,是他們當初在你身上進行鐵皮人心智控制的時候,電擊過頭,你有點腦傷,容易昏倒罷了。誰叫你接光明會偷夾在太空計畫裡的機密研究?大爺我知道你這人愛科學,但人不作死就不會死。好啦,你的學生們快醒來了,去準備你的課,去去。」史瓦利擺出「我的病人都是傻子我頭大」的無奈表情,揉揉額頭。
「可是老人們嫌我講的太難,睡鼠們又沒反應。」鐵皮人科學家委屈地道。但史瓦利沒聽,死活拖著經濟學家,一腳踹開治療室的門,又碰的一聲把門關上、反鎖。科學家望門興嘆。
診療間內,學者沒學者樣、醫生沒醫生樣,兩人零傷害力地彼此扭打,菜雞互啄。醫生叉住經濟學家的鼻孔、學者揪住醫生的領帶。史瓦利胡亂道:「好好好,剛剛說到銀行濫放貸款;得來容易的錢,的確能夠造成短暫的榮景。比方說,被利率極低的貸款沖昏頭的冰島漁夫,跑去買了兩塊地跟一棟豪宅……等到這些地與豪宅被銀行沒收,國家崩壞之後,別國政府大可以在一旁放風涼話……給我冷靜下來!」
經濟學家煩躁蹦跳不已。史瓦利見他壓不住,順手將病歷寫字版朝他頭上揍了一下。經濟學家依然蹦跳不已。
「講完資產,現在講負債。負債恆等於你身上『屬於別人的東西』,所以存款人的錢相當於銀行的負債。奇妙的狀況出現啦!銀行的資產是他人的負債,但別人的財富就是銀行的負債。
資產減去負債的空間就是『權益(equity)』,它們能換算為股東持有的股份。權益歸零,股東的老本敗光,企業歸於破產。因此負債跟權益的比值就是『槓桿』,槓桿就是你能冒多少『風險』。銀行的資產好壞取決於貸款獲利。這時候問題來了--
若借錢者的信用評等很爛,借錢給他的風險高,他付出的利息必然很高,那麼它就是個營收很好的好資產。如果信用評等好,貸款給對方的利率就低了,那麼這是個壞的資產。如果我希望資產好,借錢的人的信用評等必須爛,那麼風險就必定高。但是既然你的資產好,你的槓桿就大,就可以去冒更大的風險。所以風險永遠只有越積越多,絕對不可能控制風險。
風險不外乎賭兩種,賭未來,賭一個東西或一家公司的未來是飛黃騰達還是一壞塗地,這是期貨與股市;賭債信,這沒什麼,就是賭某信用評等極爛的傢伙,還得還不出貸款本金。
『衍伸性金融商品』就是在賭債信。某甲的信用很爛,我這家銀行十分擔心他賴帳,於是我廉價賣掉某甲的一部份債權A,你可以平白無故收取高額利息,條件是,當某甲到期還不出本金時,你要賠償我。就這樣,銀行不管貸款給何種白癡,都沒有無人還錢的風險。
你買了A之後,吃了半年的利息,覺得賺飽了,還可以把A轉賣出去,賣給了老王。老王心想,你當我恐龍嗎?甲的債信這麼爛,又已經被你啃過半年。於是你心生一計,把某乙的債權B整個賣給老王,雖然B風險很低,故沒那麼好賺,至少乙一定會還本金。於是A+B變成了C,老王終於心甘情願買下C。
問題來了,某甲與某乙不見得是人,有可能是某產業的一群企業,整個國家,甚至一大批無能力清償,依舊貸款買房的受騙三級貧戶;你跟老王也不見得是散客,而是投資銀行,國家央行,或金融操盤公司。這些一個一個衍伸性金融商品被東包西包,包到後來,可能成份複雜,龍蛇雜處,亂七八糟,根本不知道誰是誰,每一包看似是划算的投資,每一包都是炸彈,因為它們本質上只是債在丟來丟去而已。
債務包裝,逢戳必爆。差就差在去戳誰,在什麼時間點戳。按照權力者的計畫發動金融風暴並不難。所有一次大爆類型的垮臺風暴,核心精神只有一個——就是某甲某乙,你我以及老王,根本沒人知道『誰能清償債務,誰該清償債務』。不斷加料的巫婆湯的設計宗旨,屬算計風險,以吃利息。既然這樣,那就乾脆爆那個最後被戳的人,大家分屍;看看雷曼兄弟那間百年老店,萬一事情來了,也不能倖免哪;其他銀行家則飽餐一頓之後毫髮無傷。只要涉足與金融沾上邊的光明會家族,財富永遠源源不絕。
至於被分屍的那位又如何?根本不知道誰還得出債有兩個結果,片面減輕這家金融機構的負債,那麼存款人或投資人的錢就人間蒸發。要不然就重整它們的資產負債表,那麼它們的資金就會凍結。偏偏它們全都『大到不能倒』,一定要保持運作;那麼惟有用納稅人的錢填補虧空一途。所以就算被分屍,還是有紅可以吃。」
史瓦利憋著一口氣一路唸完,經濟學家已經聽到睡著了。
史瓦利撥了撥落在額前的淡金色長髮,吁了一口氣,道:「真是,你的進步一小步,就是大爺我跨得要死的一大步。拆解完全心智控制者的指令都沒那麼囉唆,偏偏越接近心靈的自由,對意志力的考驗越重哪。」
男護士正雙手端著早餐盤,可能在治療室外頭等候已久,不耐煩地踢了踢門。史瓦利連忙開門,一看,大失所望道:「為什麼不是大波護士妹子?」
「女護士們都不敢接近醫生你。」
男護士無視史瓦利生氣嘟嘴,將麵包與牛奶在一疊疊病例中騰了位子放下,又看了看在治療躺椅上睡著的經濟學家,道:「醫生你只是想讓他別鬧,為什麼不用操縱手指令就好了?」
史瓦利翻看下一個接受解除心智控制者的病例,一邊道:「濫用那種禁錮人心的東西,怎麼可能使人自由呢?史可拉笨蛋常說,操縱手指令的確可以安頓他們,那樣就失去我們努力的意義了。」
男護士正想說他不是那個意思,只是如果史瓦利的病人又亂摔東西,療養院就真的沒經費了。大夥兒最大的金主史可拉托夫,近來談到錢,就索性左手指、右手指把耳朵堵起來,開始啦啦啦。
晨光從輕輕抖動的百葉窗簾縫裡流入,史瓦利穿著雪白的醫師袍沐浴其中,悠哉地圈圈轉他的旋轉辦公椅,一邊用彩虹小馬領帶擦眼鏡。天大的麻煩,史可拉托夫都能化險為夷,總歸沒他的事。
男護士知道上校把他慣得毫無危機意識,講不通,聳聳肩便離去了。
這座僻靜的療養院位於莫斯科西南方,近烏克蘭的清幽隱密處,設備極為先進,用物昂貴。正當的經費來源,只有接受優渥退休俸住進這間療養院的退職文官老人。餘下費用,包括精神科醫護人員,僅剩史可拉托夫獨立支撐。上校總是有辦法在最後一刻生出錢來,維護得相當良好。
「我們治療他們,但不能收前光明會眾們的錢。這些傢伙的帳戶一動,國際銀行家們通通都知道了。我們是盡己之力,解放這個世界。」先知總是這樣告誡史瓦利。
這塊被參謀長劃定的醫療建設用地,受溫柔的松林環抱,差一點被別的大官擄走蓋私人渡假村。一夜暴雨將針葉林洗得蔥鬱。挺拔樹木之間散落細細的白光,將塵霧照成新娘的薄紗,一切靜得像天籟無形,流淌於天地。
史瓦利拉開窗簾,讓層層丘陵低調的綠意透進來。他用這幅景致配早餐,啵兒爽的,樂不思美國。不遠處,一對前凸後翹的儷影現身森林石板小道。門房警衛對史瓦利發出警戒通知。
「不要緊,我已經看見她們了,是笨蛋上校的戴娜貓們。」史瓦利朝著對講機道。
「那我看是她們要警戒你。」警衛道。史瓦利嘻皮笑臉地摩拳擦掌,色狼之右手準備吃豆腐,厚臉皮之左手準備跟笨蛋上校伸手要錢。
[HR]
【參考資料】
John Lanchester 約翰‧蘭徹斯特,大債時代,國內出版社:早安財經
【本章後話】
本圖取自Duncan氏的「共濟會的儀式與管理,第三版(Masonic Ritual and Monitor)」,這是皇室拱門共濟會的「第二階秘法掌管者(Master of the Second Veil)」的儀式手勢,叫作耶布侖使者的隱藏之手(Hidden Hand of the Man of Jabuhlun)。根據C.C. Zain在《共濟會儀式的古文明考(Ancient Masonry)》一書中的說法,此手勢的由來如下--為了使人類也能達成最高等的三位一體,擁有神一般的智能,必須知道「神」除了神G.O.D這個字以及耶和華YHWH以外,第三個失落的名字。這個名字雖然被視為亡佚,但可以用耶布侖Jabuhlun或 Mahabone(希伯來文的意思是「蓋神殿的石匠」)來替代。
耶布侖因此是耶和華賜給新世界的神/超人,他更勝於耶穌,也就是耶和華賜給普通老百姓/羊群的牧者,因為耶布侖這個名字至善,同時也至為邪惡,因此是超越善惡,惡因此等於善的一種表現。耶布侖的使者在世上的任務,就是替「所羅門王」建立新的耶路撒冷。
--Texe Marrs, Codex Magica: Hidden Codes of the Illuminati
雨果 Victor Hugo/玫瑰十字會、錫安長老修士會會眾

法國大革命後的激進份子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(中間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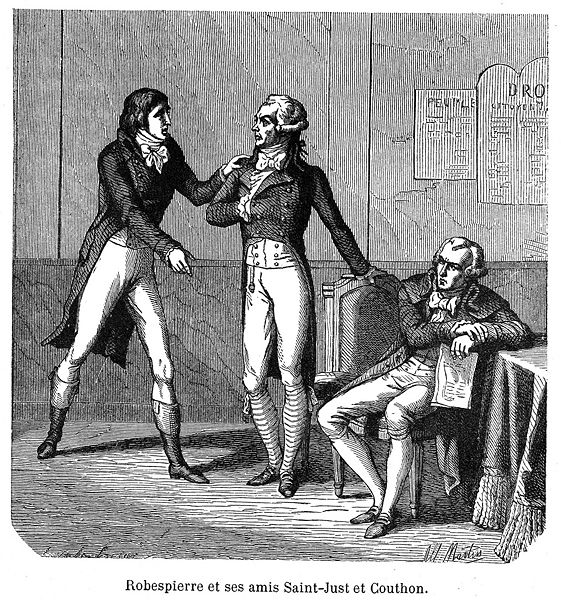
土耳其國父凱末爾

薩羅門‧羅斯柴爾德 /Salomon Rothschild

莫札特(奧地利共濟會支會會眾,據說是貴族會眾Franz von Walsegg 為了警告其背叛,匿名要求他創作安魂曲。安魂曲的創作停在「審判日,悲愴日/Lacrymosa Dies Illa」莫札特即告死亡。)

歌德/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

馬克思/Carl Marx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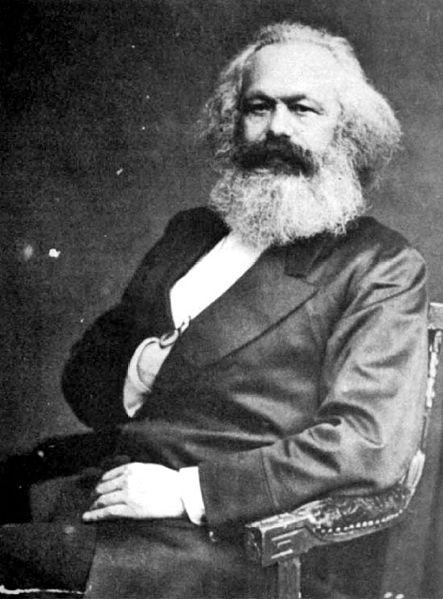
尼采/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(自幼即是會眾)

其餘族繁不及備載。
[HR]
※待續/隔週末更新※
前往下一章節

